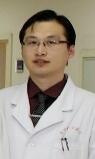 三甲
三甲
叶奎
副主任医师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血管外科
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7407人已读
近年来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已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由于其可以并发肺栓塞,导致病人猝死,或造成血栓后综合征,影响生活质量,其早期诊治日益受到重视。更由于很多DVT病人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与体征,其相关辅助检查又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其诊治方法因地、因人而异,给DVT的早期诊治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必须提高对DVT的重视程度,掌握早期诊断方法,采取及时恰当的治疗措施,对抢救病人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1.初发性急性下肢DVT的诊断
许多DVT病人缺乏典型的临床表现和客观证据,约64%初发病人没有临床症状,而有症状的病人中仅1/4超声检查或静脉造影阳性。有学者称:这种没明显临床症状的DVT为“沉寂的杀手”。所以DVT的早期诊断并非易事,但仍需遵循病史-体检-辅助检查的程序。
1.1临床评估
主要包括病人的症状、体征及DVT的危险因素。典型症状表现为突发单侧肢体肿胀、疼痛,;沿深静脉的压痛以及红斑、紫绀等,这是由于静脉阻塞或血管周围炎症所致。而类似的表现也可见于表浅的血栓性静脉炎、软组织感染、贝克囊肿破裂、腓肠肌血肿、急性膝关节炎、以及腹膜后恶性肿瘤或纤维压迫左髂总静脉、隐匿性股疝或大腿肿物压迫股静脉。
下肢深静脉原发性肿瘤或静脉壁发育不良等,需与其相鉴别。这时DVT危险因素的评估就显得至关重要,随着伴随危险因素的增多其发生DVT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恶性肿瘤、近期大手术或创伤史、近期住院史、长时间制动、妊娠及产褥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史以及明确的血栓形成倾向是重要的危险因素。肥胖、吸烟以及长途跋涉是次要的危险因素。
应用临床模型使DVT的临床评估标准化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第一个评估DVT发生可能性的临床模型是由Wells等在1995年首先提出的,他们将门诊怀疑DVT的病人根据其危险因素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三组,有DVT典型表现以及至少一个危险因素的病人发生DVT的可能性为85%,而没有典型表现及相关危险因素的病人发生DVT的可能性仅为5%,表1是其原始临床模型的简化,主要包括9点内容,应用起来较为方便。此“9点”临床模型较为客观,适用于住院病人以及门、急诊病人。近来Wells等将此临床模型的诊断程序进一步简化,将病人根据临床评分分为两类:临床评分≤1为无DVT,临床评分>1为可能发生DVT,很多人接受此“9点”临床模型并应用于门、急诊病人的诊断,还有将第9点(可替换的诊断)去除,变为“8点”临床评估模型。
表1 评估发生DVT可能性的临床模型
危险因素 临床评估
1合并癌症(治疗中或治疗后前6个月内或姑息治疗后) 1
2瘫痪、局部麻痹或近期下肢石膏固定史 1
3近期卧床>3天或大手术后4周内 1
4沿深静脉走行的局限性压痛 1
5整条腿肿胀 1
6小腿周径肿胀侧较正常侧>3cm(胫骨结节下10cm处测量) 1 7限于患肢的凹陷性水肿 1
8浅静脉显现(除外静脉曲张) 1
9有可替换的其它诊断或可能性大于DVT的诊断 -2
注:对双下肢均有症状者以症状重的一侧肢体为准。评估DVT发生的可能性应计总分,高危≥3;中危1或2;低危≤0
1.2静脉超声和D-二聚体检测
诊断DVT最有用的客观检查是静脉超声和D-二聚体检测,结合临床评估可大大减少静脉造影的必要性。
1.2.1静脉超声检查 对“中危”和“高危”的病人静脉超声检查应列为首选。B超对症状性、中心型DVT诊断的敏感性为95%,特异性为96%,对周围型DVT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为60%和70%。超声的主要缺点是其对周围型DVT诊断准确性低。当临床可能性为“中危”或“高危”而超声检查为阳性时,DVT即可确诊,而当临床可能性低且超声检查阴性时即可排除DVT的诊断。相反,当临床可能性与超声结果不一致时,DVT发生的可能性为14%~63%,这时就需要其它的辅助检查。
1.2.2 D-二聚体检测 对“低危”病人D-二聚体检测应列为首选。但由于其特异性较差,妊娠、感染及肿瘤病人也会升高,所以D-二聚体阳性并不能确诊DVT,相反,D-二聚体阴性却可以用来排除DVT。目前检测D-二聚体应用最广泛、最可靠的试验是两种快速酶联免疫吸附法,即ELISAs及SimpliRED D-dimer,前者的敏感性在95%以上,后者约85%。
早期的一些临床研究显示“低危”病人D-二聚体检测阴性时,即可排除DVT,不必再行超声检查,因为这组病人中3个月内出现症状性DVT者不足2%。这样23%-40%的可疑DVT病可避免超声检查。
1.2.3 连续超声检查或静脉造影 当临床评估、超声、D-二聚体之间不吻合时,应采取连续超声检查或静脉造影进行随访。临床评估为“中危”或“高危”,而超声检查阴性时应注意腓肠静脉血栓。孤立性腓肠静脉血栓占症状性DVT病人的15%~20%,而未被查出的腓肠静脉血栓约有20%会在1~2周内向近心端发展。连续随访可以发现向腘静脉蔓延的腓肠静脉血栓。5~7天内随访复查B超,若症状加剧或无缓解应早日复查。超声随访中1%~2%的病人可发现血栓,而此类病人在随访期间发生致死性肺栓塞的危险是0.06%。
对于不能超声随访、症状较重或“高危”病人以及心肺储备功能较差的病人应行静脉造影。另外,难以解释的整条肢体肿胀而超声检查阴性时应注意孤立性髂静脉血栓,因为下肢静脉超声不常规检查髂静脉。当然难以解释的整条肢体肿胀也可见于妊娠、盆腔巨大肿瘤或近期腹腔手术史的病人。
极少数病人临床评估属“低危”而超声检查阳性,这时应重新进行临床评估和超声检查。由于技术或其它原因超声图像质量较差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时往往凭经验,如血管壁增厚以及存在大量侧支循环时往往考虑陈旧性血栓的可能性大。若超声结果不肯定时应行静脉造影以确诊是否为DVT,静脉腔内充盈缺损即为血栓形成的证据。若静脉造影后诊断仍不明确而又高度怀疑DVT时,可以边抗凝治疗边超声随访检查肢体远端静脉。
2 孕妇DVT的诊断
孕妇患DVT时不易诊断,因为:(1)增大的子宫可压迫左髂静脉致左下肢肿胀;(2)孤立性髂总静脉血栓可致下肢肿胀而超声检查难以发现;(3)为避免胎儿受到辐射应尽量避免静脉造影检查。所以应首选超声检查,当高度怀疑孤立性髂静脉血栓而超声检查难以明确时可考虑静脉造影。尽管造影时胎儿受到辐射,但由于髂静脉血栓漏诊而致胎儿肺栓塞的风险超过胎儿受辐射的风险,故必要时仍应行造影检查。
3 DVT的推导式诊断法
根据临床模型的评估、D-二聚体的检测以及静脉超声检查的结果可以对DVT进行流水线式的推导诊断(图1)。“低危”病人首选D-二聚体检测,D-二聚体阴性则可排除DVT而无需超声检查,D-二聚体阳性则进一步行超声检查。对“中危”及“高危”病人首选超声检查,超声检查阴性则以D-二聚体帮助筛选;D-二聚体阴性则排除DVT而无需随访,D-二聚体阳性则超声或造影随访。此方法简化了DVT的诊断程序,使一部分病人避免了同时行D-二聚体及超声检查,从而节省了医疗开支。临床医生不应被此模式所限制,应结合临床进行诊断。例如病人症状加重时应尽早复查B超而不要等到5~7天,临床“高危”病人小腿症状较重而超声检查阴性时应行造影检查。另外,临床高度怀疑DVT而来不及等待多项检查结果时可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进行经验性抗凝治疗。
症状或体征怀疑DVT时
↓
临床可能性评估
∣
-------------------------------------------------------
↓ ↓
“低危”病人 “中危”或“高危”病人
↓ ↓
D-二聚体检测 静脉超声检查
∣ ∣
-------------- -------------
↓ ↓ ↓ ↓
阴性 阳性 阳性 阴性
↓ ↓ ↓ ↓
排除DVT 静脉超声检查 诊断DVT D-二聚体检测
∣ ∣
------------ --------------
↓ ↓ ↓ ↓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 ↓ ↓ ↓
诊断DVT 排除DVT 静脉超声随访 排除DVT
∣
------------------
↓ ↓
阳性 阴性
↓ ↓
诊断DVT 排除DVT
4 复发性DVT的诊断
复发性DVT的诊断程序同初发性DVT的诊断类似,但前者的诊断更困难,因为目前尚无有效的临床模式,残存的血栓使超声或造影更加复杂。
复发性DVT的临床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血栓后综合征的病史,二是目前的抗凝治疗情况。血栓后综合征病人难以区分到底是慢性症状的急性加重还是复发性DVT。抗凝治疗时,若国际标准化指数(INR)在治疗范围内则复发性DVT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晚期肿瘤病人以及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者即使INR在治疗范围内,也有DVT复发的可能。
DVT病人1年后复查超声50%以上深静脉仍不正常,所以若无以前结果对照,单纯超声异常难以明确是否为复发性DVT。
不能被超声探头压瘪的静脉段处的新病变提示有复发性血栓,以前病变段静脉受压后直径较前增加4mm以上者提示此处存在复发性血栓。而静脉造影时腔内充盈缺损即可诊断为DVT,不需与以前结果进行对照,但静脉造影技术要求高,不宜反复使用。除静脉造影和超声外,CTV的检查已逐渐在开展。
D-二聚体的检测在复发性DVT的诊断中同样具有意义。当超声正常而D-二聚体阴性时不考虑复发性DVT,当临床评估、超声检查及D-二聚体三者结果不一致时同样应进行超声或造影随访。复发性DVT的流水线式推理诊断方法如图2。
5 治疗:主要包括抗凝、溶栓、手术取栓三大类。
因充血性心力衰竭,感染性疾病,癌症,慢性肺损害等疾病而住院的患者在很多地方对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的预防是疏于管理的,在北美多中心使用超声多普勒进行联合调查了5451名深静脉血栓住院患者,其中3894名(71%)在住院期间未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在这些患者当中,2295(59%)是非外科病人,远远多于外科手术和外伤患者。共同的并发疾病比例如下:高血压(50%);癌症(32%);血栓复发(22%)及神经损害(22%)。
深静脉血栓的治疗目的主要包括预防肺栓塞,降低死亡率,减少血栓后遗症的发生。初始治疗是始于肝素或低分子肝素的投与,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血栓的蔓延,Barritt and Jordan是静脉血栓抗凝治疗的基础奠基人,他们随机调查了35名诊断有症状性肺栓塞的患者分别给予和未给予肝素处理,结果发现25%的未经肝素治疗的患者经尸检证明死于肺栓塞。另有学者证明联合使用肝素和维生素K拮抗剂可有效的减少血栓的蔓延和复发。
随着低分子肝素的引进和推广,已经逐渐替代了肝素在治疗中的地位。相对于肝素,低分子肝素只需在皮下注射即可得到很好的生物利用度,具有一个更长的半衰期,可预测的抗凝效果,而不必进行常规的每日监测凝血功能,从而大大简化了静脉血栓的初始治疗。维生素K拮抗剂(以法华林为代表)作为深静脉血栓的后继治疗药物主要用来预防血栓的复发,鉴于维生素K拮抗剂的治疗窗口很窄,为了确保治疗效果必须进行凝血功能检测,低于治疗剂量会引起栓塞的可能,反之则会引起出血。
最新开发的新型抗凝药物显示出了更持久的半衰期和更快的起效时间,fondaparinux(戊糖)和idraparinux,对凝血因子Xa具有一个靶向作用,直接抑制凝血酶的产生;而ximelagatran(西美加群),作为一个口服抗凝剂,对凝血酶介导的纤维蛋白原转化成纤维蛋白具有抑制作用。这些抗凝药物的出现,给临床治疗深静脉血栓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由于投入临床较短,目前还不清楚对孕妇和合并恶性肿瘤患者的影响。
抗凝药物可以防止血栓的进一步扩展以及改变内源性纤维蛋白的酶活性使血栓溶解,而确立了抗凝治疗在静脉血栓治疗中的地位。但是研究证明,大约有40~~70%的患者在病后一年仍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静脉改变,提示我们血栓溶解的时间和程度对患者预后的重要性。
相对于抗凝疗法,溶栓治疗的潜在优势是更快速,更完整的溶解血栓,来改善症状;减少血栓栓塞的发生;预防后遗症的产生。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尽管在溶栓药物剂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作为一线溶栓药物的链激酶,尿激酶以及重组组织型纤维蛋白酶原激活剂(rt-PA)在短期疗效上可使30~~60%的血栓得到溶解(链激酶为58%;尿激酶为48%;rt-PA约为30%)而单纯用肝素抗凝治疗大约只有7%的患者溶解。同时有关证据也指出,尽管rt-PA理论上具有一个针对血栓的靶向作用,但是对照链激酶和尿激酶,在溶栓效果上并没有区别。
溶栓治疗在给药方式上主要分为全身给药和局部注射,局部注射主要分为两种方式:患肢深静脉注射和导管介入溶栓。理论上,局部深静脉注射在血栓溶解速度和程度上要高于全身给药,在药物剂量上及出血风险上远远低于全身给药。但有限的证据表明,有两个随机研究显示局部深静脉注射和全身给药在疗效和安全性上并没有有意义的区别,不支持局部给药方式。尚未完成的研究显示,一个多中心的473名登记患者使用导管溶栓治疗,其中287名患者在溶栓前后的静脉描记上显示了一个超过50%以上的较好溶解,其主要并发症为出血(11%),其中39%为穿刺点出血。
总之,比较抗凝治疗,深静脉的溶栓治疗上看到了一个较好的短期疗效,也伴随着出血的高风险。数据表明早期的血栓溶解似乎预示了患者的预后情况,虽然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在静脉血栓后遗症的发生率上溶栓治疗要由于抗凝治疗,但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而且,不清楚的是这个较低的静脉血栓后遗症发生率是否要优于伴随的出血风险和治疗费用的支出。目前较为公认的看法是溶栓治疗不是静脉血栓的常规治疗方法,除非有严重的下肢栓塞。
在抗凝溶栓治疗的同时可应用七叶皂苷钠(麦通纳)注射液,该药具有提高静脉张力、促进静脉回流、改善静脉淤滞状态的功能,起到了抗炎、抗渗出、抗水肿的作用,对于DVT伴发淋巴水肿,尤其对抗凝溶栓有禁忌的患者具有较好的疗效。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静脉血栓的诊断,预防和治疗上,其研究成果不外乎是死亡率,血栓的复发以及出血等等,很少有人注意到运动对深静脉血栓的影响和运动对深静脉血栓后的恢复。Shrier对301名患者进行了调查,其结论是深静脉血栓后一个月开始锻炼并不使后遗症形成变得更坏,相反要好于三个月后轻微活动状态,超过50%的患者在四个月内都恢复到了其平时状态。
手术治疗和单纯抗凝治疗相比,静脉取栓术能改善静脉通畅性,可减少静脉反流和血栓形成综合症。从历史上看,手术治疗具有良好的近期疗效,对于保护瓣膜功能具有积极意义。但手术治疗有较高的血栓复发率,以及仍需长期抗凝等。而且仅有极少数临床对照试验进行了手术治疗和单纯抗凝治疗的比较,对于手术取栓对瓣膜功能的近期保护具有一定的改善,但远期效果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仅部分静脉瓣膜功能的检测指标好于保守治疗,并随着时间差异逐渐消失。
国内支持手术治疗的研究多为临床观察性试验。因此目前对于手术取栓的常规应用还缺乏证据。目前普遍得到更一致的手术适应证是股青肿等髂股静脉血栓症状严重,有致肢体坏死危险患者。手术取栓目前有股或腘静脉切开取栓术和下肢深静脉顺行取栓术。现在手术的安全性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但无论哪种方法,都应注重术后的抗凝。
局部导管溶栓理论上溶栓效果优于全身用药,具有更高的溶栓效率。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证实,而且也有报道导管溶栓与局部和全身出血有关系。如容易发生穿刺部位血肿、AVF、假性动脉瘤等。因此不能作为常规的治疗方法。其他一些微创的血栓消溶方法如超声和机械性血栓消溶正处于发展应用阶段,还有待于临床实践证明。
应该指出的是下腔静脉滤器是一种有效的减少致命性肺栓塞的措施。但下腔静脉滤器的益处主要体现在急性期能减少肺栓塞,但远期静脉血栓栓塞复发率高。因此目前主要用于抗凝治疗有禁忌或有并发症或者充分抗凝治疗的情况下反复发作血栓栓塞症的患者,且进口滤器价格昂贵,应严格掌握适应症。
本文是叶奎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仅供健康科普使用,不能做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请谨慎参阅





评论